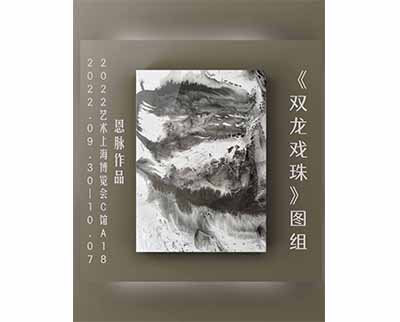引 子
(文 / 著名评论家 阿诺阿布)
新石器时代的一天黄昏,黄河边上老官台的土著往烧制的陶罐上轻轻一抹,彩陶横空出世,独步天下的中国焦墨技法也就诞生了。多年前,在北京做《笔墨纸砚》杂志主编的时候,我时常和画家朋友们这样神侃。后来写剧本《画家村》,采访了众多艺术家,这种认识竟然一天天丰满,同时也在岁月的流逝里一天天封存起来。当代水墨在中国一步步泛滥,画坊上下,是人是鬼都在玩水墨,仿佛已经争夺了国画的半壁江山,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那些满纸的肥猫瘦鸟,大块烟霞,我都无话可说,觉得国画和书法一样,给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带偏了。有时候去美术馆或参观画展什么的,见到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也大多陈陈相因,凭空虚造。千画一面的现实,与我心目中一万个画家应该有一万种笔性的认知相去太远。
直到有一天,在龙里参加一个书画活动,见到色枯先生苍茫大气、势不可挡的枯墨大作荷花系列,坐井观天的我才被拯救出来。不管业内如何喧嚣,如何抱残守缺,渴望突破,渴望创新的画家还是大有人在。
一、 色枯(张贵东)先生的枯荷
荷花是中国画永恒的主题。有关荷花的作品,浩如烟海。荷花亭亭玉立的高颜值,以及出尘不染的小资风格,一直深受艺术家追捧。人们平常所说的拈花一笑,一花一世界中的花,大多指的就是荷花。在今天,估计已经很难考证第一朵荷花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远的不说,自八大、石涛、张大千、李苦禅、张仃以降,所谓秋荷、风荷、雨荷、朱荷、墨荷、枯荷已经被各位大师写尽了所有状态;没骨,工笔,写意等等技艺,也被大师们穷尽。要在千千万万的荷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朵,多少人水干墨尽,纸废三千,穷其一生也一事无成。
色枯先生的荷花系列,不是在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荷花,也不是在复制历朝历代的艺术家们为我们打下的荷花印记。扑面而来的豪放气象,破纸而出的情绪和变幻多端的枯墨,一扫时常所见的柔弱萎靡之风,很容易就将人代入画面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高度忘我的张力之中。传统的点、皴、染对线条的信赖被消解,线条的作用被削弱,甚而色枯干脆让墨的思维凌驾于线的思维之上。墨的节奏,墨的天趣控制了整个画面,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荷的原初生命和高洁。可以说,色枯用最直接的意象造型,赋予了荷花出世的绝对精神。
老实说,一幅画,直接让人进入心境体验,从精神层面与人展开对话,这是大多数画家无法做到的。
二、当下水墨
一般来说,水墨画上手容易,但要画出精神风骨,那却是万里挑一的事。朱耷的白眼向天,徐渭的泼墨大写意,齐白石的虫虫蚂蚁,黄永玉抠鼻子的农夫,他们耸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波涛,为人类留下了一件又一件艺术魄宝。不管这些艺术品造型如何夸张,笔墨如何奔放,本质上,它们不过是水和墨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黑和白有其深刻的文化指向和内涵,它并不是简单地呈现和再现,画家追求的也不是表面的对物的理解和表达,事实上伟大的画家都是通过对物的抒情来表达精神上的享受和觉醒。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画艺术语言的特质,也是水墨最为根本的文化精神。而当下的水墨画,大多徘徊在物的层面,迈不过神的门槛。太多矫饰堆砌的画家,太多炫耀技术的画家,太多的匠气和雷同,我们很难看到个性的苦难的欢乐的怜悯的作品,真情实感的普遍缺失,人文关怀的普遍缺失,使得传统水墨走入一种今不今,古不古的尴尬局面。那么多的花,并没有几朵真正在绽放;那么多的鸟,没有几只能真正飞起来。大多数画家迷失自己,跌入了靠堆积色彩、曲意夸张的境地。
如果说传统画家深谙笔墨关系,能够精笔妙墨地传递其默想情感,那么,抽象水墨更需要画家运用如泼如舞,如狂如醉的表现手法,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披露作品的无限意味。这要求画家不但要有出神入化的线象语言表现能力和墨飞色舞的墨象语言表现能力,更需要画家有深厚的学识素养和文化品质。这两方面的欠缺,导致中国水墨甚至是导致中国画满纸荒唐、百病横生。这也是近几年来,抽象水墨表面上热热闹闹,实质上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因为,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
色枯先生的精妙在于,他在所谓的墨分五色之中,找到了发力点。
三、 色枯(张贵东)先生的枯墨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有一年在杭州采访花鸟画家何水法老师,对于中国花鸟,他认为没有一只好鸟,没有一朵好花,主要是画家的生活一方面与传统背离,一方面又与时代脱节的原因。“笔墨当随时代”、“笔墨等于零”的争论十分激烈,可惜烟花过后,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几幅灿烂的作品。已故艺术大师张仃先生将枯墨山水推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在枯墨花鸟这一块,出类拔萃者鲜有所见。我之所以认为色枯先生在诸多画家黔驴技穷的今天找到其独特的发力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判断。
其一, 色枯(张贵东)先生是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地的画家。
前面说过,中国画,其实就是水墨的关系。而枯笔,几乎去掉了水墨中更容易宣泄更容易洇染的部分,而将纯粹的墨作为唯一的艺术表现,用黑和白来完成对物的表达和倾述,对画家而言,这本身有很大的不可确定性。墨分五色,指的是在水的作用或操控下,离开水来用墨,单凭枯、涩、干、留白等手法来释放画家的所思所见,那不是简单的干中求湿、燥中取润所能体现和创造的,这也是大多数画家宁愿抱着传统的淅沥奔放、勾皴晕染不放也不敢放墨一试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大多数画家抛开一切章法造型,走上狂热追求肌理表现和新技术新工艺的不归之路的原因所在。色枯先生在枯墨中倾注了别人无法达到的激情和意趣。他的荷,他的兰,他的鹩哥,他的桃花,无物不有浓厚的抒情性和代入感。他充分利用焦墨的特性,在作品中创造性地表露出了当今画家很少触及的每一个物种所特有的图腾气质,可以负责任地说,色枯将笔的轻重缓急、一顿一挫;墨的枯涩厚薄,燥润干湿用到了极致。
南方气候湿润,常年山青水秀,要画出悲壮苍凉的枯墨,他所付出的努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好在他宽厚的文化准备和自省心境,打破了自然生态和艺术生态之间的制约,真正地体现了所谓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再者,独辟蹊径,一间孤行,这本身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画家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门。
其二,高度的概括能力造就 色枯(张贵东)先生的作品与众不同。
我有一张色枯先生的小品,画的是一枝桃花下的八哥。古往今来,画八哥的画家不计其数,他们对八哥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色枯的绝妙之处在于,他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抓住了八哥的瞬间感情。八哥躲避、自信以及无意间流露出的得意,被他勾画得维妙维肖。从这个角度而言,徐悲鸿早年所倡导的写实主义,这些年来,很大程度上被人们误读。我向来是反对那些一只手都画不准,却要对手进行千百种解构的说法和作派。客观地说,通过形态画出神态,是一个画家毕生的追求,这并非是弱化形,不要形,它反而需要画家具有高超的造型能力,只有通过准确的造型能力,通过虚实相生所营造出来的意象,才有可能使作品具有无限表达的可能。 天真浪漫的情趣,独立的审美价值,精神上的自由和消遥,这是那些事先把小鸡小鸟画在手机里,创作时看着手机临摹的画匠所难以享受到,也难以体会到的。
唯一遗憾的是,色枯先生有了脱俗忘我的生命态度,但是其作品情景相生的韵味还嫌不够,空灵之气略显不足。如果能够再吸收一些民间艺术,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养分,站到另外的山头,我想视野和心灵上的张力,都应该会宽广得多,丰富得多。
尾声
按民族人类学观点,贵阳是一座移民城市,建省至今,区区不过六百余年。色枯先生祖籍山东,父亲是南下军人。本名张贵东,江湖人称水歌,色枯是我看过他的画展之后给他取的名字。虽说他从一个涩男开始就在贵州休养生息,山地民族的诸多弱点,三线城市艺术家的诸多毛病,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他举着一年四季刮得精光的大脑袋,宽袍大袖隐居在老城区小十字——那可是红尘中的红尘,目前贵阳烟火气最足的地方。当我们坐在小酒馆,或在一些风花雪月的场合,我爱开他玩笑,他通常不痛不痒地接几句,便亮着一双看破红尘、欲罢不能的眼睛,笑咪咪和人碰杯,任由我愤世,任由我忧国忧民。
“枯哥,昨晚把我喝醉,有意思吗?”
“不要闹,我在睡觉。”
放下电话,我在想,市面上那些淅沥的水墨,大多是一种假象,因为在今天,每一个中年男人的内心,其实都是那么的枯寂。
关于画家
张贵东,男,1963年生,笔名水歌,专攻中国花鸟画,现为民革党员,民革贵州省中山画院副院长,中国对外交流中心注册画家,广东岭南艺术学院(研究员)特骋教授,中国书画院(贵州分院)副院长。
展览情况:
2014年,台湾高雄,嘉义,画展。
2015年,中法绘画交流展。
2016年,德国慕尼黑沙龙展。
2017年,广东东莞个人花鸟画展。
2018年,深圳个人花鸟画展。
2019年,广州个人花鸟画展。
2019年,广东艺术博览会画展。
2020年成立北京画馆张贵东艺术馆。
2021年作品(殘荷)被瑞典皇家画院永久收藏。
2021年色枯(张贵东)先生北京花鸟画个人画展。
获奖情况:
2020年荣获亚洲文化艺术奖。
-
展讯 I “棋实媒友”——董子棋艺术沙龙展
在当代艺术多元共生的浪潮中,青年艺术家董子棋携其漆画、油画与综合材料作品,以一场... -
以传统工笔勾写都市中的抒情,鲍莺展“花开有时”
2月7日,“花开有时——鲍莺作品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对外展出。 -
抽象唯一,中美抽象艺术交流展在上海隆重举行
2026年1月18日下午,“抽象唯一——上海夏威夷抽象艺术交流展暨上海抽象画会成... -
风云际会——上海抽象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图片简史
风云际会——上海抽象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图片简史 -
鲍莺、金江波、史依弘荣获“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艺术家”称号
鲍莺、金江波、史依弘荣获“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艺术家”称号 -
抽象唯一,上海唯一——上海夏威夷抽象艺术交流展暨上海抽象画会...
抽象唯一,上海唯一——上海夏威夷抽象艺术交流展暨上海抽象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大展